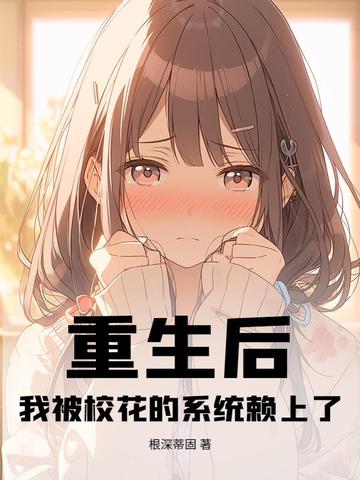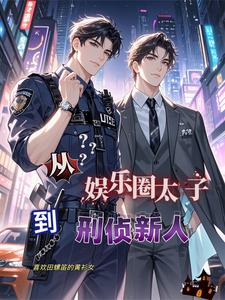首发:~大學證釋經文
或者但謂聖人不在位則不及政者,以當時之官令言也,故有思不出 位之訓。蓋非指學也。如在下位而僭論上之政令,或干犯君上,而自以 政令強人以從,則犯上作亂者矣。得謂之知政乎?故聖人但論為政之 道,與夫治平之方而已,非謂干政也。
《論語》謀政者干政也。不可不知!古者聖主詢于芻蕘,國之賢 者,皆得以其所學貢之君上。何有不論政之語?即夫子謂仲弓「可使南 面」,亦以其才學,明於治不之道矣!設後世儒者,將謂之為犯忌甚 矣,而不知夫子雖為此言,原為大公無私。初非使弟子覬覦神器也。
故坐而論政,為平居之教學,使出而執政,則致治平反掌耳!若所 學不逮,一旦從政,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之喻也。焉有不敗者乎?故聖人 為教也,至廣大而盡精微,立高明而道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備具。此 所以成聖人之教之大,而見道之用之廣也。
【亞聖孟子講述】
夫子講齊家在修身一章,以家齊由於一家之人,各能自修其身,則 各安其居,各得其所,而無不和不睦之事矣!惟齊家者,不只為一家 也。家者,身之所託;國者,家之所寄。故齊家必及治國也。治國與齊 家原本連貫而言。
故本章先以堯舜之仁,能使人從以仁;桀紂之暴,亦能使人從以 暴。可見一身之所繫大矣!
身之修者,天下尚從其化,而況一家之親者近者乎!故本章言齊 家,全重在修身。亦如前章言修身,全重在正心誠意也。能誠正者,上 可格於天神;下可化於萬物,而況身之五官百體,不能使之夷然自得而 無所損乎?故身以誠正而後修;家以身修而後齊;國以家齊而後治。其 道一也。堯舜之仁,由於誠正;桀紂之暴,由於反誠正。而一身之故, 遂致天下皆從而化之。則身之關於家國可知已!身若不能自修,而責家 人之能從,是反其所好而令之也。反而令之,惡且不從,況善耶?以見 君子齊家,必自修身始。
且家雖非國與天下比,然已非一身也。上而父祖,中而昆弟,下而 子孫,以至於夫婦、姊妹之儔、僕婢之類,其繁者,同族長幼姻戚男 女,或眾或寡,決非一人可比。要皆使之無間,心悅誠服,以安以和, 則必有道以致之矣。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皆重在 自修其身以化之耳。
本經自此後皆言教化。故教化必自家始。由近及遠,由親及疏,教 之道也。所謂令及喻,皆指教也。人多不知此處為教言,而錯列前格物 一段,遂使聖人重在以身作則,推其教化,由家而國而天下,以成其明 明德之功、之旨,不可復明。斯可惜矣!
【宗主孚聖疏述】
曾子講述之文,以聖人述教。自格致至治平,本係聯貫說去。為學 者自初學至成功,明德明道本末功夫,皆盡於八條目。後人遂以為聖人 教人,人人皆須治國平天下,豈非以官吏為志、帝王自居者乎?而不知 聖人言教與學,皆以道為本,以天為則。天無不覆,道無不生。故聖人 於人、於物,無不欲成之。而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成人成物,使各得其 所,各遂其生也。
《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天下飢,己飢之;天下溺,猶 己溺之。」此皆聖人之所志,皆法乎天,本乎道之所為也。不必有國, 而不能不為治國之學;不必有天下,而不能不求平天下之方。伊尹、周 公之心,與湯、武一;益、稷之志,與堯、舜同。雖其位不同,其所學 一也。故孟子有「禹、稷、堯、舜,易地皆然」之言也。於此可見聖人 所學之廣,亦可知所成之大。而所學、所成者,非聖人私之一人。聖人 望人無不聖,故其為教,亦必與己所學、所成者同。此乃明明德之極則 也。
夫聖人自修身而後齊家治國平天下,雖若有先後。其實言其方耳! 致治之道耳!非若修身之於誠正格致也。蓋齊家而後國治,治國而後天 下平。係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非身已修則家無 由齊;非國己治則天下無由平。此就本末言,而以事理衡之也。
但為學者則不得以此為次第也。如既修其身,則須學齊家之道;既 齊家矣,則可以學治平之道。然不得謂家尚未齊,不得學治國;國尚未 治,不得學平天下也。蓋能知修身之道,則齊家易矣!能知齊家之道, 則治國易矣!能知治國之道,則平天下易矣!其本既立故也。若曰: 「吾未嘗治國,不可語於治天下也。」遂不復志而學之,則背聖人之教 也。故曾子有分學與教之論也。蓋修身以內,但就為學言;修身以外, 則就為教言。故其先後雖分,究不可不明聖人設教初旨也。
修身以內,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先後不 可差也。修身以外,能齊家者即能治國,即能平天下。以事之本末言, 則不可舍本逐末;以為學言,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以致之。不必待 先成於此,而後學於彼。如以此先後為學,則不在位者,不必為治平之 學,而平居者不得論家國之政,豈有是哉?故曰以言教也。教者舉政而 言,故為教者必由家而國,不可躐也。亦如誠正必自格致始也。
再由學言之!至誠正身修,其大本己立。如是以之治事,事無不 理。故齊家則家齊;治國則國治;平天下則天下平。蓋為宏其用而已, 不限於其事也。故君子在位則為堯、舜;在野則為伊、孔,不必事功同 也。其能致治平之效,亦不必以政令也。教行而天下化,是即平天下之 功。故聖人無不有明德之全,無不合天地、齊日月者也。皆因其有誠正 工夫,身修無虧,道全、德全,而足以致之也。
即如道、佛二宗之教,亦以成道之後,而普度世人,欲人成仙佛, 共登極樂者。其旨亦同。蓋己即成道,則遇事皆隨措而無不宜。其成功 至易,以其本立故也。為學者,無論志為仙佛、為聖賢,必先立己之 本,而致身成道。然後用世可以致治平;為教可以化草木,無所往而不 見其德。此所謂明明德之極則也。故曰:「皆自明也。」非自明德,何 以明於天下?非自成道,何以使道行於天下?故各教皆以修持成道為急 務。而儒教必以誠正修身為本基也。
自齊家以後,皆須措其用於事。故述之較詳。非如修身以內,為事 之簡也。修身以內事,自秦、漢以來,儒者多不能習之,使道、佛潛修 之說勝。而修身以外事,道、佛二家之徒多不講求。遂指為儒者所習。 皆失之也!蓋道無不包舉內外。內功、外行,缺一,不得為道之全。如 天之春冬、日之晝夜,皆相須而成者。為教而僅用其一,是偏其德也。 皆後人誤解聖人之旨也。新教力矯此弊,內外俱重。尤以誠正為本,此 義直貫天地古今。為至道、為極德。雖有聖人再起,亦不得廢之矣。
再,曾子雖言分教與學,然仍是一貫。不可誤為兩截。要知皆教 也,皆學也。不過一以學言,一以教言。其先後次第始易明也。
述齊家治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利,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 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 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 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以上述齊家治國
(今本)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也。
一家興,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謹按:今本列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自「堯舜帥天下」起,至 「未之有也」止,現移前修身齊家章。又詩云上「故治國在齊其家」 句,現刪。一家節「戾」改「利」,理由見後。
【宣聖孔子講義】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一節,仍舊!中一節已改正,移於前 章。「故治國在齊其家」,係重出。可刪!下即引《詩》三,仍原本。 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止,為一章。
此章係述治國之要。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可以治國;家 不齊,則不可治國。其理,以國之本在家。本立而道生也。故本章先言 齊家之效及於國者。國與家比,國大家小。然積家而成國。家皆齊矣, 國焉有不治者乎?且此處非僅言治法。蓋重在教!教固,並及於政。然 必先理而後事。以理言之,教之能行於其家,方可化於其國。若家猶未 服,奚以使國人從耶?故治國必先齊家。
即以事言之,家為國本,家之為教也易,其政也簡,其人親,其物 近,情易通也,性易盡也。故必先之。先家而齊矣,而後推之於國,亦 如推修身之道以齊家者然。先近而遠,由易而難,事半而功倍也。況家 齊而人皆法之,取譬於家,人皆有其家,人皆以自齊其家,國無不齊家 矣!舉國皆能齊其家,則國何有於治平乎?然國雖如家,而猶有異者 焉!故齊家者,猶未可謂之治國也。必也推其齊家之道,以治國耳。此 君子必推其所為焉!本章首稱「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即所 謂立本者也。
次言「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即所謂以家為人效法者也。下 言孝者三語,即所謂推齊家之道以治國者也。《康誥》諸語,皆述齊家 之效足以治國之理也。蓋齊家之道,必先以一身為則。身正則人自誠 服,以盡己而修其身,以推己而及於人。忠恕之道已備,家自隨而齊。 盡己以齊其家,推己以治其國,亦忠恕之行,而國焉有不治者乎?知此 義,則知人心正如我心,人情可得,人性可盡,而教之必行,令之必 從。不待先有其國,或先有其位,而後言治者也。
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赤子者,盡己 推己之謂也。不遠者,教必行,令必從之謂也。茍能如此,豈必有國有 位,而後能言治乎哉?故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此言家為國人表式。「一人貪利,一國作 亂」,此謂由己不謹,而國人相率為亂也。雖言齊家,仍不離修身。身 可以為人法,則其家亦可以為國式也。再細求之,不獨一家也、一身 也。即一言之微,猶可僨事,而一人之德即可定國。其相應有如此。故 君子欲國之治,可不自修其身,齊其家乎?身之於家、於國、於天下, 皆以忠恕行之。則欲仁而仁,欲讓而讓。仁、讓由己,而國人從之俱 化。此為善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反之,則以己之貪利,小人相效, 而爭奪以起,一言害德,而人相率而背畔,為惡之效亦不期然而然矣!
故聖人為己,時自警惕,恐或動於惡而召覆亡。此堯舜之所以治 也。小人不知天命,不能敬畏,逐物徇欲,妄作妄言,而致眾畔親離, 家亡國滅。此桀紂之所以亂也。故治、亂之機,在己而不在人;在自立 其德,而不在貪其利;在先示以仁讓,而不可妄言以惑眾也。
夫一人定國者,聖人而王者也。言足以為民法,行足以為民則,重 仁讓、先禮教,利當前而不貪,欲在物而不蔽,兢兢自持,惟勤惟謹, 而后人懷其德、化其教,政行而民安。雖與之天下,無不平矣,況一國 乎?故君子為治,知高位之不易居,大權之不易握,身在民上,必自待 以下,德為民望,必謹慎以審言察行,思治日亟,則不敢圖功;居位日 久,則不敢貪利;明天之道也,順性命之正也。天無為而能恒久,不息 之道也;性無物而自光明,不染之道也。惟能無為,始合天道;惟能光 明,始順性命,皆自修身致其功也。故君子以道為治,以天道為政,以 性命為教。天從而民不違,性正而物皆順。此聖王之治也。不教而民 勸,不令而服,況教之、令之者乎?故君子處萬事而無所容其心,平天 下而無所用其智,垂供而治,不慮不思而無所遺,不貪利而得天下,不 圖功而治其國。蓋能本乎天道,適乎人情之至者也。堯舜之謂也。
故儒者為教亦同,勵己而化行,修身而教施,天下無不從其言,感 其德。一言而為後世法,一行而為後世則。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 不尊親。不必有其土地,不必居其權位,而民奉之如神,敬之如天。蓋 其德所致也,非竊名貪功者可語也。故聖人為教,不強人以從,不嚴法 以迫人,不夸以示人,不以外而忽內、末而忘本。皆順性之正,率天之 道也。
故其成功也,無功而功莫與大;無名而名無與齊;無利而天下皆利 之;無為而無不為;無德而德自大;無道而無不適於道。教之極,化之 至,無世界方域之殊,人民風俗之異,皆將崇而奉之,信而行之矣!
【又曰】
自一家以推及一國,固如一身推及一家。惟國中政教極多,須使人 人均能率從,故非以身作則不可。言之為效,不若行也。為國者必事事 慎戒,處處謹循,以為眾法。蓋一人之邪,足以為國之亂;一人之正, 足以致國之治。其影響至大,又非僅一人之得失、一家之禍福也。故堯 授舜位,而告之以「天之曆數,在之躬,四海果窮,天祿永終。」舜、 禹皆亦然。皆誓於天以明其志,不敢少違其訓。其重天命,即重民命 也。故克享天命,而四海永甯。
聖人為君,未嘗敢肆其心,兢兢業業以持其躬,匪伊朝夕,靡有自 逸,其治乃大,其明治平之道也。蓋道者無不平,在上者必下其心,道 乃不危。茍自以為君而虐其民,自失其德,而示民無德。是亂也。故治 國之要,在以一人為天下責,不可以天下為一人責。堯舜之戒慎,非有 所迫也,非為名也。以其道耳!合道則聖,背道則昏。桀紂之昏,以天 下惟吾獨尊,惟所欲而莫予違,遂敢為暴虐,荼毒其民,而民欲與俱 亡。故身殘國敗,而天命莫續也。
故君子為國,必自戒慎恐懼,有德以式於民,以契於天。即不在 位,亦如是以為教。使遠近咸服,莫不隨化。故身在家而教成於國也。 身在家而教成於國者,無他!以其善推所為耳!人之性同秉於天,其德 同。以吾德感,無有不同化者也。《書》曰:「如保赤子。」正以赤子 全其性,德皆同也。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即仁也。仁,性德之大者。推 其仁,則國皆化而仁;推其恕,則國皆化而恕。茍推之無盡,化亦無盡 矣!
故君子求諸己之所得,施於人無不應。故曰:「雖不中,不遠 矣!」夫同化之效如此。君子不患無其位也。茍修其身以及其家,雖不 出家而教日以遠,不必先求之人也。女子雖在家,而夙夜承父母之訓, 其嫁也,自能善其生育也,亦以其教之化同。其所化者應也。君子雖不 在位,教且行於全國;其仕也,自能善其政令也。豈必先政令而後可仕 哉?故君子為政,只在教中;而為教,只在推性之德耳!
故治國在齊家;齊家在修身也。茍明此道,則修其身者,即為齊家 治國者也。齊其家者,即為治國平天下者也。只在本吾性德,推吾仁 恕。在家則教行,在位則治成,無往而不化,無往而不從。此君子之學 本於己者也。《詩》所云:「宜其家人」。宜其家人,已齊其家矣!故 可教國人也。如桃之葉蓁蓁者,由於其花之灼灼。其華之灼灼者,由於 其樹之夭夭。而樹夭、華灼、葉蓁者,其實未有不蕡者也。正謂人之能 立其德者,其家人無不宜。家人宜者,其教自可及國人也。
下之「宜兄宜弟」,及「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諸語,皆此義也。 人既宜兄宜弟,是家人無不宜矣!其可以教於國人者,即在此。其儀之 不忒者,其教之可化於國,亦可知矣!蓋其家人如父子、兄弟,皆足以 為法。而民亦從而法之矣!此即教之化及於國,而莫非由於身之德及於 家人也。
宜兄,謂善友;宜弟,謂善恭。父子、兄弟足法者,謂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無不可法也。此齊家之至,而即治國之所自也。
夭夭,指樹。此《詩》以桃之夭夭,比人之善修其身、立其德,而 足以齊家以教國人。莫不由於本之先立耳!本立者,其枝榮、其華灼、 其實蕡,其應必矣!人而能立其德,修其身,齊其家,教自化於國。其 應亦如之。故曰:「治國在齊家。」
【宗主孚聖附注】
本章「貪利」,原誤為「貪戾」。 宣聖以治平不能不謀人民福 利,故後有生財大道,及以義為利之訓。然恐在上者,因爭貪一人之 利,而忘大眾之福利,是必啟爭奪之禍而亂作矣。故孟子以梁王尚利而 告以其害。王好利,則以下者無不隨之利己而圖。而利有盡,欲無窮。 此所以爭奪也。故曰:「不奪不饜。既相奪矣,欲不為亂,得乎?」 此 夫子所謂「一人貪利,一國作亂」者也。觀於今世,此語尤信。茍 望無亂,必在上者不貪!
述治國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