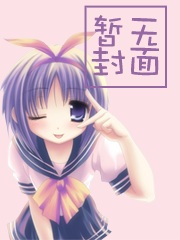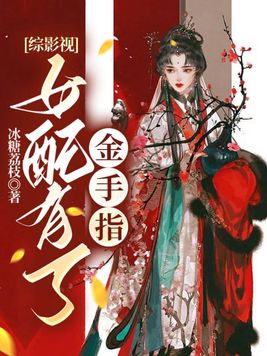首发:~第84章 李密桃林兵变被杀,实乃死于自身的“羞耻心”
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长安城笼罩在初冬的薄雾中,银杏叶泛着金黄树叶金黄,犹如披上了一层“金甲”。太极殿巍峨的飞檐上,晨霜未曦,在朝阳下泛着微光,熠熠生辉。
殿内正在进行大型朝会,这是唐朝开国后的第一个冬至大朝会,意义非凡。皇帝李渊非常重视此次大朝会,新朝初立,急需一场盛大的典礼来昭示天命正统,于半个多月前便已安排专人精心准备。
而在这场精心设计的政治仪式中,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为这场朝会增添了几分微妙的气息——他就是三个月前归降的瓦岗军首领李密,此刻正以从三品光禄卿的身份,准备完成他人生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一次使命。光禄卿主要职责之一便是负责皇宫的日常饮食和操办宫廷酒宴、大型礼仪等。这个职位在唐代是一个从三品的官职,虽然地位较高,但对于李密来说,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羞辱。
朝堂之上,李密站在百官行列中,绯色官袍下的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玉带銙,心中五味杂陈。
在五更三点(约凌晨4时),皇宫承天门外已是一片肃穆。百官身着朝服,依品级列队。李密也已站在九卿之列,深绯色的公服在晨曦中格外醒目。他的目光扫过队列,昔日的瓦岗旧部徐世积、秦叔宝、王伯当等人,如今都已换了新朝官服。
寒风中,李密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象牙笏板,指尖触到冰凉的质地,心中泛起一丝苦涩:曾几何时,他手持百万雄兵,如今却要在这朝堂之上执庖厨之役,他感觉光禄卿的铜印在腰间愈发沉重。
辰初(7时),鼓乐齐鸣。太极殿内,李渊端坐龙椅,冕旒下的目光深邃难测。太常卿奏起《昭和之乐》,群臣三跪九叩。李密随着众人俯身行礼,额头触地的瞬间,他仿佛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回响。礼乐声中,他分明感受到无数道目光在自己身上游移——有审视,有讥讽,也有同情。
鸿胪寺引导诸州朝集使、蕃邦使者进献祥瑞。当徐世积献上黎阳嘉禾时,李密的瞳孔微微收缩。那金黄的稻穗在殿中熠熠生辉,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瓦岗军昔日的辉煌。他注意到多位大臣的目光在嘉禾与自己之间来回游移,嘴角挂着若有似无的笑意。
巳正(10时),典礼进入高潮。李密率光禄寺属官二百人,以朱漆食床抬御膳入殿。子夜时分,他已亲自验看过\"太牢\"三牲(牛、羊、豕各一),用银匕一一试毒。此刻,他手持象牙笏板前导,八名主膳抬着鎏金步辇,内置青玉食案,食器铭文武德年号的唐制云纹。
行至丹墀九阶,李密止步,由殿中省尚食接递。他跪地奏道:“光禄臣密,谨奉天膳,伏惟陛下饮和食德。”
李密的声音在殿中回荡,他感觉自己的尊严仿佛也随之消散在空气中。
当他捧着金漆食盒趋步丹墀时,分明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嗤笑——昔日统领百万瓦岗军的魏公,如今竟在御前执庖厨之役。
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当日御膳特设“混一南北”之菜——洛阳水席头汤\"牡丹燕菜\"与太原醴酪同案而陈。
太原醴酪,又称醪糟,是一种传统的山西小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味。根据《礼记·礼运》中的记载,“以烹以炙以为醴酪”,说明在古代,醴酪是帝王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食品。
在寒食节期间,太原地区有食用醴酪的习俗,这与纪念介子推的传说有关。虽然传统的醴酪制作技艺在当代有所演变,但其作为太原特色小吃依然深受人们喜爱。
这道菜品的寓意再明显不过,皇帝李渊要以李密为媒介,收服山东势力。李密望着案上的菜肴,心中五味杂陈。他明白,这不仅是一顿御膳,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而自己,不过是这场大戏中的一个道具。
“陛下圣安。”李密的嗓音有些发涩,手中的青瓷碗盏映出他微颤的眉峰。
(注以上内容是作者按照《大唐开元礼》溯推当时情景,有不足之处读者朋友们可以提出修改建议)。
殊不知,此次献食成为李密叛唐导火索。《隋唐嘉话》载其退朝后愤言:\"吾手持百万貔貅,安能作长安庖人!\"未及半月即借收抚旧部之名东出潼关,终酿桃林之变。司马光评曰:\"高祖使密典膳,实察其志,若养鹰饱则扬去,惜乎调饥未得其术。\"
这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冬至朝会,既展现唐初礼制建设成就,亦暴露新朝整合山东豪强的困境。李密在献食仪式中的尴尬处境,恰成隋末唐初权力重构的鲜活注脚。
退朝时,李密特意绕道西内苑。西内苑是唐代皇家园林之一,位于太极宫的北侧,具有军事防卫、游乐、生产等功能。苑内筑山,挖有四处池沼,沿池建有亭阁楼榭,为帝王日常游憩场所。根据历史描述,西内苑的范围南北约一里,东西与宫城齐。
李密进入西内苑,却见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早已候在那里。王伯当与李密在瓦岗军时便十分亲密。李密当即把心中的委屈和感受到的耻辱告诉了王伯当。
王伯当心中郁结难平,眉头深锁,这位左武卫大将军解下兜鍪,露出鬓角斑白,对李密沉声道:\"魏公,天下大势尽在您运筹帷幄之中。如今东海公徐世积坐镇黎阳,襄阳公张善相据守罗口,河南各郡精兵强将,皆是我瓦岗旧部。这些力量,只需您一声号令便可调动,岂能长久困居长安,屈居人下?\"
暮色渐深时,李密独坐府中,案上摊着山东诸郡的舆图。襄阳王弘烈在罗口屯兵五万,张善相镇守伊州,秦叔宝、程咬金的旧部散落河南道各州——这些名字在他舌尖滚过,恍若当年金墉城头猎猎作响的旌旗。
更漏三响,李密忽然起身,蘸墨在奏疏上写下:\"臣虽驽钝,愿效班超之志,宣圣威于山东\"
次日太极殿内,次日朝会,他整肃衣冠,向李渊进言道:\"陛下对我恩重如山,但我一直闲居京城,没有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实在感到惭愧。山东地区的将领们,大多是我以前的部下,他们都可以为朝廷效力。我请求前往招抚他们,借助陛下的威望,一定能一举平定王世充。这个逆贼盘踞在洛阳,表面上看起来势力很大,实际上外强中干。在我看来,打败他易如反掌,就像弯腰捡起地上的小草一样简单!\"
皇帝李渊早就得知李密的旧部将士大多不想依附王世充,虽有张善相等将领表面归顺王世充,实则心怀异志。退朝之后,李渊便找来近臣商议批准李密去收抚他们。
李渊端坐御案之后,目光深邃。
裴寂率先进言:“陛下,李密此人,狡诈多端。昔日在瓦岗,先投翟让,后夺其位;归顺宇文化及,又反戈一击。今若放虎归山,恐难再制。”
萧瑀附和道:“正如将鱼放入清泉,纵虎归于山林,必不复返。”
陈叔达更是直言:“李密素有枭雄之志,山东旧部十万之众,若使其重掌兵权,恐生肘腋之患。”
阶下谏议大夫魏徵正色道:“昔者韩信归汉,终遭未央之祸。陛下岂不见宇文述旧事乎?”
李渊轻抚长须,目光扫过众臣,缓缓道:“卿等所虑,朕岂不知?然帝王之位,自有天命。纵使李密有二心,也不过是蒿箭射蒿,终难成事。今王世充盘踞洛阳,李密素有旧怨,若使二贼相争,我军便可坐收渔利。”
皇帝李渊深思熟虑后,决定派遣李密前往山东,去收拢那些还未归降的李密旧部。命人将李密召入宫中,告知准予其招抚计划。
李密听闻此讯,心中既激动又忧虑,因为自己已另有打算,边伏地叩首边向皇帝请求道:“此番前去任务艰巨,臣希望贾闰甫能与我一同前往。”
皇帝李渊沉吟片刻,见李密态度坚决,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又命人将贾闰甫召入宫来。
殿内焚着龙涎香,李渊命李密、贾闰甫两人一同登上御榻,这在当时是莫大的殊荣。内侍奉上金樽美酒,李渊亲自为二人夹菜斟酒,语重心长道:\"朕与卿等共饮此杯,以示同心。大丈夫一诺千金,朕既许卿东行,必不相负。纵有朝臣反对,朕亦当力排众议,朕愿以真心相待,绝非他人能够离间我们君臣之情。望卿等勿辜负朕的心意,建功立业,以报国恩。”
李密、贾闰甫闻言,赶紧跪拜受命,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李渊看二人神色,随即又命王伯当为副使,率精兵三千随行,并特赐李密御马\"飞白\",以示恩宠。
李密与贾闰甫详装感动不已,连忙再次拜谢接受命令。
是夜,李密与王伯当密议于府中。王伯当低声道:\"主公,李渊此举,名为重用,实为试探。我等当如何应对?\"
李密凝视着案上的地图,手指划过潼关、桃林,沉声道:\"李渊欲使我与王世充两败俱伤,我岂能如他所愿?待出潼关,自有计较。\"
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一日,长安城外朔风凛冽,旌旗猎猎。李密一行整装待发,随行有贾闰甫、王伯当等心腹,以及三千精兵。
临行前,皇帝李渊特赐御酒,又命李密将半数部众留驻华州。
唐初的华州,即现今的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地理战略地位。华州(古称郑国)在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设立,当时称为华山郡,治所在郑县(即华州区)。在华州的历史中,名称曾多次变更。例如,唐武德年间一度改名为太州,但不久后又恢复为华州。此外,华州还曾改名为华阴郡,但使用时间也不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华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称华州。唐初,华州辖郑县、华阴、下邽三县。唐末,还曾短暂地将栎阳县划归华州,但时间很短。
华州位于长安以东180里,是关中地区的重要门户,东距洛阳670里,是唐代长安与洛阳之间驿道的必经之地。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华州被称为“通化门前第一州”。由于华州地处关中军事要地,唐肃宗时期在此设立了镇国军节度使和潼关防御使,管辖华州和华州的军事事务,确保这一战略要地的安全。
华州在唐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华州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唐代许多着名诗人都曾吟咏过华州,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王昌龄等,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杜甫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期间,还写下了《题郑县亭子》等着名诗篇。
唐初的华州不仅在地理和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丰富的文化和文学成就也使其成为唐代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皇帝李渊命李密将半数部众留驻华州的决定,笔者觉得,唐高祖当时是不是唯恐李密不乱?这一决定看似是对李密的信任与重用,实则暗藏深意。这一举措,既是对李密兵权的削弱,也是对其忠诚度的试探。
李渊早已觉察李密心思,也明白放虎归山易,收虎入笼难。此举既可防止李密坐大,又可观察其反应。
李密何等精明,岂会不知其中玄机?当他接到这道命令时,心中警铃大作,暗自思忖:“李渊真是老狐狸,此举分明是要断我臂膀。若我抗命,便是授人以柄;若我顺从,则实力大损。\"
于是他面上不显,只是恭敬领命,甚至主动表示:“臣蒙陛下厚恩,自当谨遵圣意。留驻华州之部众,将以待陛下调遣。”
这种表面恭顺、内心警惕的态度,正是李密在政治博弈中的生存之道。在长安这个权力漩涡中,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因此,他选择隐忍不发,暗中筹谋,等待时机。这种微妙的心理活动,既展现了李密的政治智慧,也预示了后续事态的发展。
张宝德也随行在列,此人素来谨慎。张宝德是李密麾下的长史。在李密决定叛唐并离开长安去收抚山东豪杰时,张宝德作为李密的部下,他注意到李密与旧部频繁密会,又见其将家眷秘密安置,再观皇上的“用心”安排,心中愈发不安。他预见到李密此行必定会反叛,因为他已经决定归附唐朝,不想再跟随李密四处流亡或遭受败亡的命运。
是夜,张宝德在驿馆中辗转反侧,终于提笔写下密奏:“李密素有枭雄之志,今得东行,如鱼入海,必不复返。臣恐其借招抚之名,重聚旧部,届时山东必乱。”
皇帝收到张宝德密奏之后,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李渊不但没有采取补救措施,比如派使臣将李密截回,或是派出精锐军队就地将李密截杀,反而降下敕书派一小卒慰劳刚出发的李密,并告知其留下带走的部队慢慢前行,让李密自己单人匹马回朝,然后再委以他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