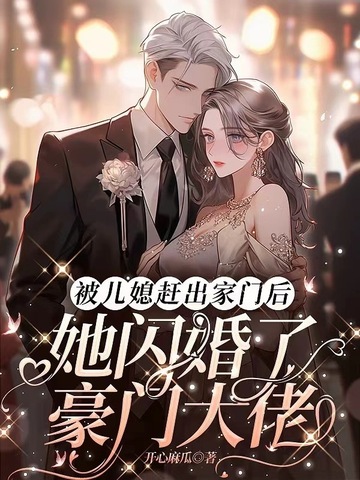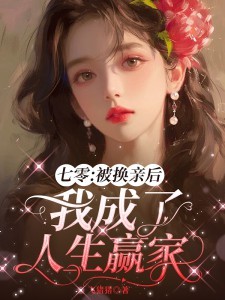首发:~第28章 孔雀东南飞之被骂了千年的婆婆
刘兰芝与焦仲卿。
是的,元希音这次穿到了著名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面了,成为其中了被骂了千年的恶婆婆焦母。
乐府诗开篇就是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一个投水而死,一个自缢于庭树。最终合葬于华山旁。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就因为这一篇乐府叙事诗歌,焦母被骂了千年。
元希音垂下了眼皮,喝着儿媳奉上的热茶。心内细细思量。
现在是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群雄并起,时局动荡,天下已经是群雄割据的地步,连年的战乱并没有让那一块地方是安宁祥和的。
受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现在的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规矩深入人心。
《仪礼》上要求了妇人有三从之义。《周礼》中还专门针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制定了繁琐而严苛的规矩。
东汉时的《礼记》还还规定了媳妇平时侍奉公婆时,不能出现打喷嚏,叹气,伸懒腰,斜站,斜眼等不规矩的行为。
焦母丈夫早亡,一个寡母带着一双儿女在这乱世里面生存,并且将儿子培养成了一个小小的府吏,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以在这么多年的磋磨之中,焦母将规矩印在了自己的骨子里,以规矩要求自己,也要求自己的儿媳和女儿。这是这个时代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这个刘兰芝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整篇诗歌中可以看到,她刚烈又极富主见,行动之间自有主意。对于婆母的不喜就要求回家,对于丈夫因为公务繁忙就开口抱怨。
这些都是婆媳之间矛盾的触发点。反而对于浑厚三年未生子的情况,焦母反而没有任何的提及。
焦仲卿这个儿子是个只会和稀泥的,在母亲和媳妇之间焦头烂额,双边互哄,反而拿不出一家之主的架势处理好这个问题。
公务繁忙不常回家是其一,家里一团糟的婆媳关系让夹心馅饼的焦仲卿打心眼里逃避回家是其二。
元希音叹了口气,放下了茶盏。感觉到嘴中的苦涩,这个年代的水真的不是怎么好喝。
低眉顺眼的媳妇儿还站在自己面前僵持着,面上似乎带着点点的倔强和不服气。
元希音脑中一转,想到了早上的事情。因着儿媳妇织布手艺好,是以给家里增加了进项。庐州府里很多的大户人家还是能穿得起细布的,是以刘兰芝日日织布,经常将布匹送到铺子里去寄卖。
刘兰芝长得好,明眸善目,又是年轻的媳妇儿,穿着打扮上就很是精心了些。原诗里就描写了刘兰芝的美: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这样的美人生在这乱世本来就是危险的,幸亏焦仲卿身为府吏,周边邻居都是多年的老邻居,没有什么邪念,反而注意保护焦家,平时焦母也拘着儿媳和女儿出门,才没有出什么事情。
今日晨起,听隔壁李家私下提醒,去铺子买布的时候看见刘兰芝送布,铺子里的有一个年轻的男子死死的盯着不放松。
焦母心中焦虑,毕竟年纪大的人了,唯恐自己儿子不在家,儿媳妇出了什么事情,是以早上吩咐刘兰芝不要出去送布,她替她去送布去铺子。
刘兰芝是个行动自专由的,听了就不高兴。但是这心中焦虑的事情,焦母也不愿意多说,看到儿媳妇不愿意的面色,直接就冷下了脸,禁止儿媳出门,就气的躺在了床上。
打量了一眼刘兰芝微微红肿的眼睛,看样子这个娇滴滴的儿媳妇也哭了一场。
元希音揉了揉眉头,心内宽面条的眼泪,不仅要感受老年人的生活,还要体会一把古代版本的婆媳关系……
系统666啥也没说,叹了口气继续神隐。
刘兰芝小心的看了一眼婆婆,见婆婆皱着眉头心内沉了沉,“母亲,儿媳今日的布还没送去呢。若是迟了……”
元希音严肃着脸开口,“你可知我为何不让你去送布?”
刘兰芝低垂下眼,“儿媳不知。”
元希音可不是那什么都不说明白只知道用孝道压制的焦母,直截了当的开口讲邻里的话语说了出来,直说的刘兰芝,面目惨白,睁大了眼睛,大大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似乎是承受不了婆母犀利的话语,摇着头,眼泪如断线的珍珠落了下来,打湿了衣襟,“儿媳绝没有做那不守妇道之事。”
元希音长叹一声,“我知你和仲卿感情深厚,虽然你平时行事自专,但也是守规矩的。这样的事情我自然信你不会做出的。”
听得婆母话中并无严厉,刘兰芝缓了缓,深深的行了一礼,“多谢母亲信任。”
元希音摆了摆手,继续说道:“我虽信你,但是却不信那个盯着你的男子,听邻里的描述,那男子仪表堂堂,身上穿着绫罗丝绸,带着配饰,想必是富贵权势之家。”
刘兰芝张口欲说,元希音直接打断,“仲卿只是个小小的府吏,咱们家只是比耕种人家好上那么一点点罢了,你这样的品貌打扮,若是那男子起了歹心,掠了你去,咱们家如何护得住你?”
一席话如晴天霹雳,直直的让刘兰芝震在了当场,这样的乱世,她也不是养在深闺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姐,自然明白乱世什么都保不住的道理。
再看看身上的打扮,婆母身上的打扮,心内一时羞愧,对早上对婆母的不敬起了懊悔的神色。
刘兰芝良久才喏喏的说道:“儿媳知错,听母亲的,再不去送布了,儿媳只在家中织布。这送布的事情就劳烦母亲辛苦了。”
元希音点了点头,刘兰芝见婆母面上没有以往的不满之色,方松了口气,将织好的布匹恭敬的递给婆母。
元希音接过了布,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东汉末年,人口凋敝,虽然是庐州府这样的大城市,人口也是稀少,路上零零散散的人走动,面上都带着战乱年代特有的惊惶不安。
就是开着的商铺,也是人烟稀少,门可罗雀。元希音找到了地方,将儿媳妇织好的布递给了东家。
东家验好了货,不经意的看了角落里坐着的男子,开口笑呵呵的问:“今日怎么劳动太夫人送来?”
元希音早就看到了角落里的男子,心内沉了沉,面上却是笑着跟东家说话,“我这儿媳不巧昨日晚间做饭的时候伤着了,今日是不能来了的。”
眼角的余光看到角落的男子听到伤着了面上担心的神色,心里有了计较。
东家继续问道,“可是要紧?请了大夫不曾?”
元希音维持着面上的笑容,“昨日太晚,只是找用土法子简单包了包,我这送完布就去给我那儿媳妇儿抓药去。”
说着长叹了一口气,“只是东家见谅,我那儿媳妇伤了手,这有段时间是不能织布的了,这布就不能经常来送了。”
东家摆了摆手,“养伤最重要。什么时候得了布再送来就是了。”
元希音含笑的答谢了东家,拿到了东家结算的钱,方走出了铺子。
面上一冷,果然那个男子不安好心。摸了摸手中的五铢钱,感受到身后的视线,脚下不慢去了药铺的方向。
去了药铺,抓了烫伤的药膏和一些别的药草,面对药童疑惑的询问,元希音和善的笑道,“我这把年纪懒得动弹,虽然是伤着了手,怕万一后期热起来,这些药先备上。”
药童见只是清热解毒的寻常草药,也就打消了疑问,毕竟也有很多人家是多抓一点药回家备着的,就怕夜间找不到大夫,总能应急。
元希音拎着药脚步匆匆的回了家。到了家门口,邻居李家就叹了头出来,看着元希音手中的药。
元希音熟练的堆起了焦母的笑容应付邻居的问询:“儿媳妇做完做饭的时候伤了手,我给抓点药。”
李家老太太抓着元希音不放手,小心的看了四周,才小声的嘀咕,“我给你说的那事,你问了没有?”
元希音抽回手,示意看了看手中的药,“这都伤了手了,还怎么织布去卖。”
李家老太太点了点头。借着小心的说道:“我听我儿子说,又要打起来了,就在咱们边上不远,不知道会不会打到咱们这里。”
元希音心内一沉,拉住李家老太太:“我儿子还没有回家,你从哪里来的消息,快说给我听听……”
李家老太太飞速的看了四周,方附耳将知道的消息给元希音说了。越说心越沉。
元希音很是好好的道了谢,然后才怀揣着一腔沉甸甸的心事回了家。
迎上来的刘兰芝看着婆婆一脸的阴沉,虽然疑惑,但是也什么都没说,接过了婆婆手中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