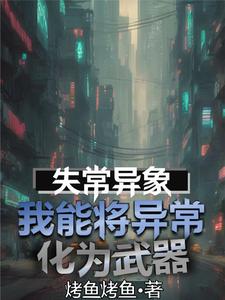首发:~第3章 郓州小吏赴汴梁,焉知是福殃
李格非当晚在王府吃酒自是不在话下,至于和王老令公(王拱辰)喝了多少酒,那就不记得了。
李格非的王府之行就这样草草了之。
李格非回到官舍,与其他外放回来的诸如晁补之,董荣等刚接到朝廷通知,下个月初一上朝,让各级官员及早准备。
不时间,已至初一,文武百官近百人分批走进宣德门,其中李格非等一应谪官列于队尾,缓缓入宣德殿,皇帝端坐,但是却因年幼,长翅帽显得格外突兀,有点摇头晃脑。在皇帝的侧畔,就是皇帝的祖母高太后,神宗去后一直是她在宫中操持,更是有力挽狂澜“除腐立新”之名。如今第一天临朝称制,威仪势必甚嚣天外。
文武百官分列两班,宣德殿庄严肃穆,高太后先言“先皇在世,太子已立,此当更无异议,赵煦乃先皇正朔,理应为大宋之主。”
台下众人皆细小声啼“是呀,是呀。”小皇帝虽然调皮,此时倒是分外懂事,一切都听主母言语。
高太后言罢皇帝即位之事,稍等片刻见各人无多言语,即讲“诸位大臣有何朝奏,速速报来”此时依然无人言语,若是在别朝国之大丧,京城百姓当是千头百绪的乱成一团才是,可是大宋与他朝不同,皇帝去只悲怜三日便可恢复如初,与常人死并无二致。大殿上静悄悄的!
当然无论如何这新旧承替,都应该有点动静才是,新皇初立,又有各类谪官入京,本该有更多事发生,而今却悄无声息,岂不是奇怪吗。实际每个人的内心都在暗潮涌动,今天必有大事发生,只是欠缺一个导火索。
河东路经略王安礼(王安石弟弟)出来说话“臣等防守西夏数十年,西夏惧我数十年,大宋可往灭之,永绝后患。”
高太后道“西夏国力微弱土地贫瘠,得之无益,况大宋立国多年未轻言灭国之战,将军之话过矣”。
又一武将说“西夏虽小,但他耗费军资已逾供辽岁币一半,辽国胃口也越来越大,恐日后难以为继。”
高太后听闻这些,显然这两个武将的话奏的都是些无关痛痒之事,今天重点不在边关防务,而在于如何清理新党余孽,这一朝文武没有人愿意开这个头,大概所有都是这样想的,高太后必须想个法子把这把火燃起来。遂问“龙图阁司马光,你认为二位将军所言边关之事当如何是处理。”
司马光不慌不忙的,甚至还抽时间理了一下衣襟,“太后,臣所述,当今之事,不在边关,而在朝内。”
旧党之人包括太后内心暗暗窃喜,终于讲到点子上了。
司马光继续说“我等在集贤馆修史数十年,研读古今,盖古今国之昌盛者,莫不是内部和谐,人心所向,所谓兵者,既耗天下之资,又伤及人命,非必要不得用兵。臣闻秦之所灭,非为匈奴之祸,汉之所丧,皆因朝堂之乱,王莽董卓之流必为祸首。至于前朝更毁于毫无才智的杨玉环杨国忠,又宦官忠奸之党不明所致。而如今我大宋之国日昌,但隐忧已显,新党急功近利,祸害臣民百姓久矣。”
高太后见司马光如此识趣,心中窃喜,有人自动将破坏先帝所支持的新法罪责揽下,实在是…,内心无可言语的痛快与喜悦,表面上却反问道“司马卿,新法之弊从何而来?”
司马光此时也许脑袋被缸砸了一下,没有明白高太后的意图,顺势又说“新法之弊,弊在急功近利,如所颁布的‘青苗法’,是当农户无钱购置良种,官府以低息钱与之,待青苗长大,收获成粮食,或还粮食,或还利钱,本无可厚非。此法在一地尚可,利于管理,推广至全天下则害之,即便是在三州五府施行,也难管理。其一,不知放出去的钱财是否用来购置粮种,其二,倘若遇到荒年,干旱,百姓颗粒无收,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肆意加码索钱,穷人家则要卖儿卖女,流氓匪户则群起抗租,勾连乡里,三五州府即被鼓动,即便没有遇到荒年干旱的人家也会抗拒,不愿交钱,至此祸患首出,新法旨在提高朝廷税收,这样朝廷不仅收不回成本,反倒引起民怨,则改其初衷。此一弊也,再说募役法,按户入伍改为按需入伍,只要有钱便可永不为伍,如此,国无兵丁,税务司源。”
高太后听完连连点头“司马卿,所言甚是,还有谁人补充?”
户部晏秋道“变法之市易法所言朝廷出钱购买天下滞销的商品,待市场需求时再高价卖出去,这样既可以赚钱,又可以让滞销商品有了去路。但实际上朝廷所购滞销商品,几乎都无法再卖出去,即便卖出去的算上仓储屋资,也所赚甚少,度支局连连亏空。更别说赚钱了。”
听了这些,秘书监黄道离急忙辩解“新法之所弊,不是因为新法设计有误,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一些官员执行不力才出现明显弊端,每一条法律执行过程中多多少少有旧党之人参与,这些人刻意故意让新法执行到一个坏处,这才导致许多律令事与愿违,每一个新法都皆为解决现有问题才设计的,况王安石公高风亮节,绝不会故意设计出让大宋出现弊政的法律。新法设计在人,新法执行也在人,这人分多种,新党和旧党就属于不同的人,新法的实施这两种人都有参与,若一味的将某一事情的失败归结为某一个某一类人,实在不公平。”
司马光刚欲再言语,只听中间一排有人骂道“司马光,你这个老匹夫,若非你指示人从中作梗,处处阻挠新法,新法不至于举步维艰!”但看那人是谁,正是王家二公子,李格非的叔父王贺之,虽然被革职,依然领秘书监从事。这突如其来的骂声惊动了整个朝堂,一众朝臣和皇帝乱哄哄的,那王贺之甚至欲动手,幸亏左右拦止,李格非在后排暗暗叹道“难怪旧党之人拿我叔父开刀,原来整一个二愣子,这种情况只会给旧党以口舌,并不能给他和新党带来任何好处。”正乱之间,小皇帝害怕跑到祖母那里,口里颤颤喊到“祖母皇太后!”看来是第一次,被这种乱哄哄的场景吓坏了。
高太后拉着小皇帝在大殿之上呼喊,“肃静!肃静!”,众人安静下来,高太后怒道“朝堂之上,成何体统,先皇刚刚仙去,你们就乱做一团,怎么面对先皇,来人,将王贺之叉出去关进开封府大牢。”
听闻此语王苑之,王拱辰扑通跪倒在地,却未等言语,高太后没有一丝停顿“御史中丞王拱辰教子无方,迁章德军节度使参将,也即刻滚出汴京。”王拱辰立地不敢说话。王苑之急道“太后,老父年迈,恐难以外放。”这边太后哪里肯听,立即唤侍卫将他两拉出去。李格非正不知所措。
还未及拉出殿门,殿外特使飞奔而来,“太后,金陵八百里加急文书!”
众人见特使急状,遂安静下来,高太后打开文书,读之却神情恍惚。却又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不免潸然泪下,这泪水掺和着许多情感,与天,与旧党斗了三十三年的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终于去世,是高兴,还是忧愤不得而知,二来突然觉得朝廷失去这么一个能力挽狂澜的肱股之臣而惋惜,三来失去了竞争对手后那种油然而生的孤独感,再有失去王安石后大宋朝廷将去向何方,如何带领大宋朝廷稳步发展的这个担子将落到这个垂垂老矣的祖母皇太后身上。高太后内心五味杂陈,缓缓的对众人叹息说道“王安石临川先生随先皇去矣!”
众臣默然,或惋惜,或窃窃私语,朝堂之上一片安静,即便是他的竞争对手也对这个高风亮节,明波清流的王安石感到惋惜。这一刻,他值得在场的每一个由衷的敬佩。
突然司马光来了一句“王安石公千古,吾等不如也!”
众臣齐声喊出“王安石公千古,吾等不如也!”
朝堂之上又归于宁静,片刻之后,高太后似有泪言的说“王贺之押入大牢三个月,望其悔改,永不得入殿,王拱辰迁彰德军节度使,念汝年迈,可居于汴京,不必赴任。所有朝上士人谪官暂不安排新职,都回去先写一篇王公(王安石)的谥文,待三日后临朝,择优者颁送王公,以纪王公之功业。”
众人拜服,遂散朝。
因为王安石的去世,朝廷停止安排谪官新的职位,让全体朝臣写祭文,这才是千古第一回,真是给足王安石的面子。
李格非和王苑之扶王拱辰返回王府。
李格非问王苑之“这二叔父性子还是如此着急也。”
王苑之没好气的回答“都是给惯的,汝二叔父却比你年轻几岁,但也有三十多了,好似还没有长大。只是爹爹这次可能气的不轻。”
李格非叹道“有子如此,也算操碎了心。”复又说“二叔父不会有什么性命之忧吧!”
王苑之答道“料也是无什么大碍,毕竟我朝伤文人性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李格非疑问道“二叔父不是革职在家吗?为何今天又出现在朝上?”
王苑之答道“还不是父亲曾经关照的三公六卿给面子,所以才……”
李格非又惭愧道“刚刚在朝上未曾言语相助,爹爹不会怪我吧?”
王苑之说“你一介谪官,以少言为好,况你言语只是多了一个人受难,并不能解我与父之窘境,甄儿和易安还等着你回家呢!我也不想你出甚状况!”
李格非闻言,遂安心回到官舍准备和其他同僚一起写王安石的祭文。
“
王公昭昭,一去天地泯然。临川易水,荡涤神州之南。七尺微躯,保国三十三;一枝秃笔,勾写无限江山;身仕浮沉,几度御风几度凭栏。御风时,身扛重担,挡烈日以驱风尘,领无数学子僚属共赴劫难;凭栏时,心所望故国,泪何以干。而如今,青衫已去,忠骨犹在。
王公生于天禧,起于庆历,得志于熙宁,元丰,亦失志于熙宁元丰,受皇天后土,皇家恩泽,几度拜相,几度力挽天下之狂澜。所谓人之所灵杰,莫出王公之右者。悠悠古今,能有几人哉。
庆历初,功名显,得益于范文正提携,却拒高官利禄,远任签判,知县,监吏,皆无品阶之利,亦无权御之益。王公意欲闻山间之鸟鸣,观陇上之牛犁,察兵民之愿遂,究税赋之所盈,盖王公之志,乃欲潜伏于天下之根本,才能瞩庙堂的高远,遂于民间见闻之有二十年余。又熙宁初,得欧阳文忠提携,乃入朝堂。王公将所写文书丞于其上,神宗闻之,惊为天人,遂召见,王公陈旧法之弊,言新法之利,‘富我大宋,强我大宋,变法之道,无非民,兵,商,吏,国;民之为根本,无民则兵,商,吏,国皆崩塌,遂以青苗,保甲,农田水利法诸法利之,兵之为拱卫,保四方家国,遂布‘募役,将兵,保马’等法;商则利也,鼓励市易,降低易税,使兴盛;吏则冗也,剪裁,消泯,得三之一可也;最后为国,国,乃君也,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君必以力之先行,而利必以后享,方可国家。此五法辅以众小法,国之强盛,可图也’。神宗闻此新法,精神大震,遂许之于羽翼,授之以权柄,躬身亲为,势必除弊兴利。新法之初,日月昭彰,利若星象。天下之人皆以新法为处理国事家事之要律,百官趋之,万民顺之,当年之星星之火而如今若此燎原,可谓人心沸腾,人事飘然。
然天不遂人愿久矣,新法逾进,则阻之逾强,青苗法本以利民,却生流民;吏减三一,则三二无所去;商税骤减,商利获多,却不见税之多也,等等,众法之所利皆成所弊。反对声起如骇浪,众民恨之,众兵弃之,众吏拒之,众商避之,唯国之所担当,然神宗与王公呕心沥血已不能挡反对之声,众口摧之,悠悠苍耳亦被反对之声裹挟,不能遂愿。王公复又归乡野,归尘世,而后拒声偃息,王公遂又起,而拒声亦起,此起彼起,此伏彼伏,俨然相生相克,起起伏伏,反反复复,王公终归这尘世的一抔尘土。
呜呼!王公去矣!天下百年难得一遇之良才,高风亮节,志比寰宇,人若仙骨,今之一去,你我殊途。
王公去兮,王公归兮,奄奄山林,若现一青衫之人,恰似曾经之少年(王安石),须臾,却又缥缈于云海隐树之间。
”
李格非写完此书,悻悻搁笔,长思天下之难,能若王公之人,天下能有几个,却也处处艰难,步履蹒跚,何况寻常人乎!
三日很快即完,文武百官之祭文也大抵也都写完了,所有文章都皆写上姓名,交由礼部监察使张简之一一编号装订,且按姓名,似科举考试一样密封上交官家。
待到朝上,文武群臣肃静,高太后先言“诸位卿家所写之祭文,大略有百篇,经枢密院和礼部监察使张简之刊合评判,再经哀家所阅,有三篇甚得人心。遂将这三篇所文公诸于众。”
第一篇:
元佑初,王安石公变法辛劳,疾病缠身,病没于江宁,因此感怀。自王公忠心为国始至没,已有三十三载,在官时,忠君体国,去官时,忧怀故国。王公性情高洁,诗文法度育人无数,吾之后生及后世,当永记之,纵观公之一生,皆为国辛劳,为国忧愁,愁满胸怀,愁到三秋,变法之力用尽公之一生所有,遂作‘江城子’以纪王公。
三十三载为国忧,恨无头,几时休。莫问归期,莫道不千秋。呕尽肝胆愁血泪,家国事,愿长留。
六十年宠辱付酒,苦还有,恨还有。只是杯中,无酒问谁求。欲取江水杯易满,杯中酒,似君愁。
高太后读完此篇,众人皆赞,深刻表现为国尽力的王公,真切的表达呕心沥血王安石一生,三十三载国事,六十年生涯,只是忧愁多生。高太后道“此篇我觉得表现力甚佳,只是用词作祭文,甚少。但我闻苏轼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一祭奠佳作,遂表为佳。此为谁所作呀?”。
这时只见人群之中靠后的一位身形彪瘦且唯唯诺诺的人站了出来,看这情形,他应该不是经常出入这种场合,“太后,此篇乃是臣秦观所作。”
众人皆叹,秦观,秦少游,词文天下早有威名,却不曾想现已立入朝班。